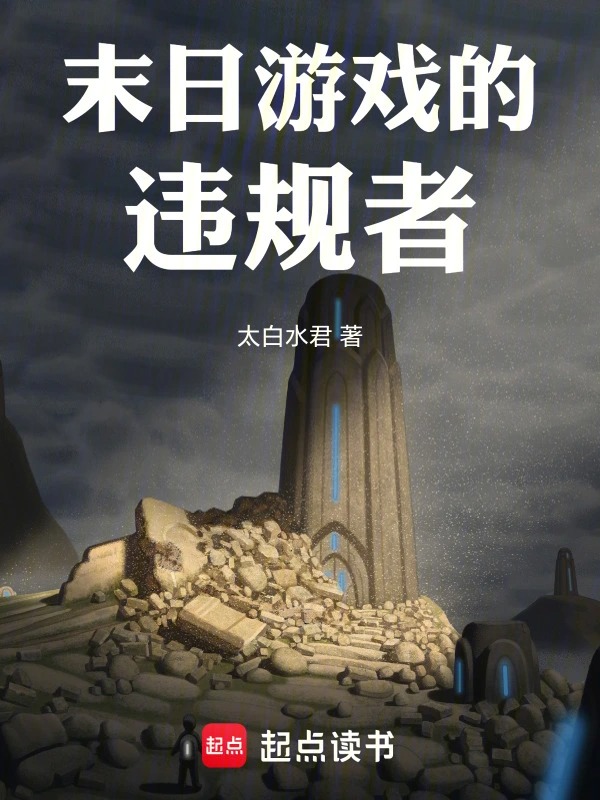第一章 要被当成礼物送人了
瑟瑟秋风扑的人面已是微凉,枯黄的树叶被风儿一卷便几乎铺满了整个院子。
云子卿和往常一样,始终是一身素白的衣衫,绸缎般的墨发随意的散在两边肩甲,漫不经心的倚着窗栏看院子里的福伯扫着落叶。
扫完一层,不多久便又会落下一层,周而复始,年年如是。
抬头算算日子,云子卿已经在这个院落里住了十二年。
十二年来,只有和福伯相依为命而已。
云子卿收回视线,看了看面前桌上的笔墨纸砚,纤细略显苍白的手,随意的磨着墨,口中叹息,叹完又摇头轻笑。
在这里待的太久,竟也学会了那些闺阁女子的多愁善感,亏他还是个穿越人士呢。
云子卿磨好墨,提起了面前的毛笔准备落下,袍子的下摆微微晃了晃,脸上没有任何波澜,手里的动作也不曾停下,却开口道:“你来了。”
静悄悄的屋子里只听得到外面人扫院子的清脆声,和毛笔碰触在洁白纸张上的沙沙声,云子卿的背后却不知不觉的站了一个人。
男子一身的锦衣华服,发丝被发冠束起一直垂到腰际,俊俏的眉目中多了一份英挺,此刻站在这里,却比不上面前一身素衣白衫好似风雪中独独开放如白梅风姿的人。
青崖低眉走到了云子卿的身侧,恭敬的施了一礼,然后从怀中拿出了一个一指宽的小药盒摆在了桌面上,微微侧眼看了面前着白衣的人,眉目在不经意间露出些许的同情,道:“国主还有一封信,让属下带给三皇子。”
青崖低眉敛目双手呈上信。
云子卿拿笔的手微微顿了顿,放下了笔,转头打量站在自己面前的青崖,轻轻放缓了自己一瞬间有些僵硬的背,自嘲的笑了笑。
他带着前世的记忆穿越而来,成了云祁国当时只有一岁大的三皇子,表面尊贵,实则卑贱,只因这位三皇子是国主醉酒后与一婢女所生。
在尊卑如此严明的朝代下,他体内一半卑贱的血液是整个云祁皇室的耻辱。
而没几年,在那些兄弟姊妹挑唆下他被驱逐出境,送到了擎苍国与普通百姓一般过着寻常人的生活,可他的命和今后的路,始终掌握在云祁国主手中。
那个,名义上所谓的,父王。
云子卿的脸上,表情始终只有淡然,道:“放在桌上即可。”
青崖放下信,目光中比以往多了一些情绪,三皇子一直不受国主待见,却因从小容貌出众才换得如今一命尚存。
因为那姿容对国主来说还有些用处。
遂,三皇子体内才被埋下了一线红,此毒阴狠,一生无解,只有靠每年送来的药,才能保他不受万蚁噬心之苦。
今年,是送药的第十二年,也是最后一年,因为剩下的药国主已送了他人。
“三天后便有马车来接三皇子,还请三皇子早做准备,属下告退。”青崖低眉向后退了几步,一个转身,施展轻功消失在了原地。
福伯扫完了院子,累的满头大汗,轻手轻脚的端着茶水走进了一尘不染,摆设相当简单的屋子,免得打扰了公子写字。
福伯轻轻的将温热的茶盏放在了桌面上,疑惑地看着那封搁在小盒子边上的信。
往年这个时候只送来药,哪有什么信啊,疑惑的瞅了瞅自家的公子,在云子卿默许下打开了信,白纸黑字,寥寥数行,一眼就能看完所有内容。
【洛公高寿,以卿之身相赠,结两国之好。】
说白了,就是把他当礼物送人了。
福伯的手不禁一抖,信掉在了地上,一张老脸气愤的通红:“这这...这不是要逼死公子嘛!如何使得,如何使得啊!”
青州国国主,洛公,已年过六旬,后宫之中姬妾男宠无数,公子前去,不过是多添个人数罢了。
云子卿仍旧一身淡漠,波澜不惊。
他以后是什么样的命,一早就清楚了,虽然是现代人,可是在这莫名其妙不是任何一个朝代的地方,他以前所学的历史根本毫无用处。
不得先机,谈何争命。
“福伯,以后的日子怕是更苦了,你不若离去罢,”他没什么可惦念的,也就这个老人陪了他十多年如亲人一般,最不愿看他跟着自己吃苦受罪。
福伯一听,更是老泪纵横:“老奴不依,老奴这一生跟着公子,虽没有荣华富贵,生活却快活,我这一生膝下无子,这些年早视公子为亲生孩儿,公子若要我离去,老奴便只有一死。”
福伯佝偻着背,跪在地上重重的磕了一头,云子卿连忙扶起了面前的老人:“福伯你这是做甚,快快起来,就当我没有说过之前的话。”
福伯一听,笑着用双手胡乱抹着自己脸上的老泪。
安慰了福伯好一阵子,福伯才平复了自己的心绪。
午后,福伯把洗的发白的旧衣物一件一件整齐的摆好在床铺上,认真叠好,开始打包,又拿出了锁在柜子里仅剩的银两,一并放进了包袱里。
福伯面容愁苦,重重叹了口气,公子虽为皇子,却是一生坎坷,家国不得住,皇宫不能回,只能在这别国的都城里苟延残喘。
想来,满心凄凉。
而如今,连这清汤寡水的日子也没法过了。
继续阅读